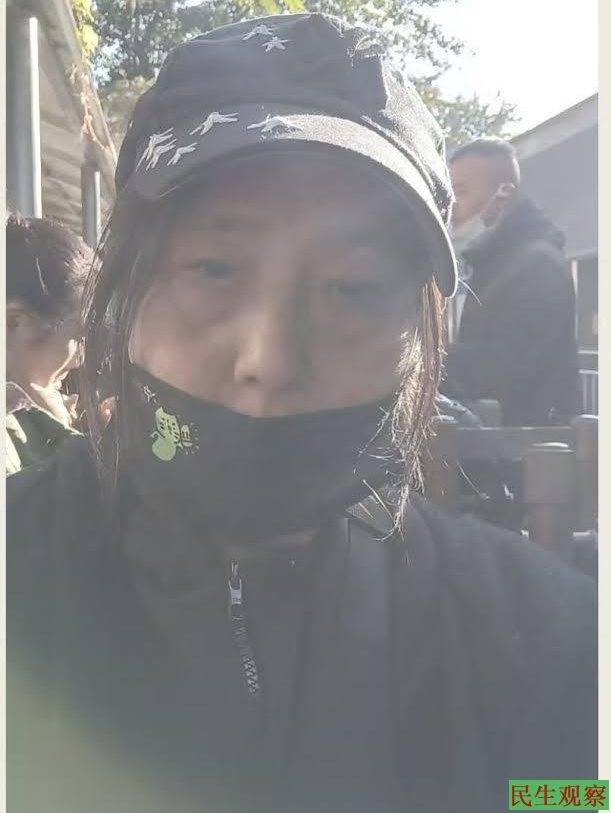除了在被拆除的新疆托库勒清真寺的遗址上建造一座公厕外,中共还采取其他手段羞辱宗教。
作者:马修·奥莫莱斯基(Matthew Omolesky)

中国似乎通过三种明显截然不同的方式镇压宗教和摧毁文化。大量基督教圣地、穆斯林公墓和民间宗教寺庙被拆除,令人痛心的悲剧比比皆是。山东第一观音像被滑稽的孔子塑像取代,河南汝州市修建了可笑而愚蠢的所谓“毛主席佛祖殿”,这些弄巧成拙的证据既让人心酸又让人好笑。最近几个月,近似低俗、滑稽的愚蠢尝试更是屡屡出现,但除了当地党委外,也许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这种尝试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
我说的“低俗喜剧”,是指最近几年的“清真寺整改”运动导致一系列旨在羞辱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幼稚举措。“清真寺整改”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实际是指有计划有步骤地拆除和亵渎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敬拜场所、宣礼塔、公墓和麻扎(坟墓),包括位于绿洲城市和田以北的伊玛目阿西姆之墓(Imam Asim shrine)等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建筑物。在阿图什市松他克村(Suntagh village)的托库勒清真寺(Tokul mosque)遗址上,现在建起了一座公厕。在阿兹纳清真寺(Azna mosque)的遗址上,现在建了一间便利店,并且店里还挑衅性储存了大量的酒和香烟。洛浦县(Lop county)一个清真寺遗址上,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活动中心,而伊里其乡(Ilchi township)一个清真寺遗址上,则会很快建成一个批量生产内衣的工厂。
在托库勒清真寺(Tokul mosque)遗址上建公厕对于任何一个有点教养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冒犯,这种行径当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当自由亚洲电台对该事件进行跟踪采访时,当地村支书不承认这样一个举动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失策。当被问到是否迫切需要在清真寺的遗址上建厕所时,这位村支书只是耸耸肩说,“各家都有厕所,所以以前并不存在这种问题。”而官方立场仍然是建公厕是为了满足“来该地区检查的督查组或者干部们的需要”。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当真。的确,这只能解读为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而该计划就是历史学家卡哈尔·巴拉提(Qahar Barat)所说的“在精神上打垮/击溃精神”。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在其1978年的小说《耻辱龛》(The Traitor’s Niche)中概述了文化灭绝的不同阶段,即:“首先,肉体上击垮反抗者;其次,根绝任何反抗的思想;第三,摧毁文化、艺术和传统;第四,消灭或者削弱语言;第五,灭绝或削弱民族记忆。”这种“慢性屠杀和持续数世纪之久的伤痛”会是一个逐渐衰弱的过程,但“与那些冷酷无情的能手所做的事相比”,也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为了研究,那些能手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守在煮人的大锅旁,或者守在将反抗者剥皮的绞刑架边。”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清真寺被拆毁后用厕所取代。维吾尔“母语”运动被镇压后,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维吾尔语言学家和诗人)不禁哀叹道:“他们口里的话并不可信,就像玫瑰花上的雨滴,一阵风吹来就消失了。”然而,大规模监禁、奴役、施加心理压力、酷刑和强制绝育等行径也日益猖狂。
达伦·拜勒(Darren Byler)在其2020年2月份发表的一篇关于被失踪的著名维吾尔作家帕尔哈提·吐尔逊(Perhat Tursun)的极具冲击力的文章里记述了他和另一个维吾尔文学家的一段对话。那位文学家非常生动形象地叙述道:
2009年后,我有一些朋友被关进监狱,有一次,他们问狱警是否可以看维吾尔歌舞视频,狱警说可以。于是,大约有30个狱友聚集在一间监室里看视频。他们很高兴,几个小时后打算回到各自的监室,但是狱警说,“不行,你们既然要求看这些视频,那就请继续看。”所以他们看了24小时的视频。之后他们再次问是否可以离开,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感到非常不舒服了,但狱警说,“不行,这是你们要求的,请继续看视频。”最后,他们看了72小时的视频。房间里弥漫着30个男人大小便的味道,最后他们说他们再也不要求看视频了,狱警这才让他们回到各自的监室。幸运的是,这些男人非常坚强,他们仍然头脑清醒,没有精神错乱。
这种已成为惯例的羞辱曾出现在采用系统化、制度化侮辱手段的纳粹集中营(Nazi Konzentrationslager)里,也曾出现在把剥光衣服的囚犯塞在“狗笼”里以便最大程度羞辱他们的苏联古拉格劳改营(Soviet gulag)里。我们不应当忘记,纳粹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建立的一座灭绝营)指挥官佛朗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1971年接受采访时曾承认,在当时那些背景下恣意羞辱他人的残酷行径并不仅仅是出于肆虐成性的本质,另外也是为了“训练那些事实上不得不遵守这些政策的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做当时被要求做的事” 。人们在新疆等地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况。将受害者非人化后再实施文化灭绝、酷刑、强摘器官、强迫年轻女性绝育自然就容易多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非人化的其实不是受害者,而是施暴者。一个是希望能和平地敬拜神灵的宗教信徒,一个是强拆清真寺并在其遗址上建厕所的政府官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再显而易见不过了。一个是要求看歌舞视频的在押知识分子,一个是连续折磨他几天的狱警,同样有着天壤之别。经历所有这些羞辱和文化毁灭仍坚持为生存而抗争的维吾尔人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维吾尔音乐教育家木沙江·肉孜(Musajan Rosi)创作的一首维吾尔歌曲这样讲述:
“艰难的旅途刚刚启程时,我们寥无几人,
穿行在沙漠里,我们最后成了一辆大篷车,
沙漠上留下了车辙印,生命在红柳树丛旁消逝,
在漆黑沙漠里倒下的英雄没有安息之地。
不要说红柳树丛旁逝去的生命没有坟墓,
他们的坟墓将在初春长满鲜花,
尽管我们的马匹羸瘦,但大篷车永远不会停下,
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使命,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前赴后继。”
在广袤而恶劣严酷的塔克拉玛干荒漠里,许许多多维吾尔人的无名坟墓四处散落,但是那些以前来到这里的人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对维吾尔公墓随后的毁坏虽是个灾难,但是单凭这个还不足以摧毁整个民族。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比所有公墓的总数还要多得多。
上文提到的诗人帕尔哈提·吐尔逊在其2006年夏天写于北京的代表作《挽歌》(Qeside/Elegy)中,也许给出了最好的描述。在哀叹“他们砍下我的头只是为了试一试刀有多快”之余,他仍然向读者保证,“当他们强迫我将屠杀当成爱接受时/你知道我也与你们同在”, “当他们在各条街上搜不到我消失的身影时/你知道我与你们同在”。正如翻译吐尔逊作品的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所说,这首诗可以作为“那些因历史上强大却致命的意识形态而消失的所有人的墓志铭”,但是“每小节的最后一行诗似乎在波涛汹涌的无情历史洪流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当作其中的救赎”。这些不朽的诗句给人带来了希望,而新疆当局则不顾他人感受,强行用一些亵渎手段羞辱民众。通过对比,大家应该能很快意识到,到底是谁在羞辱谁。
来源: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