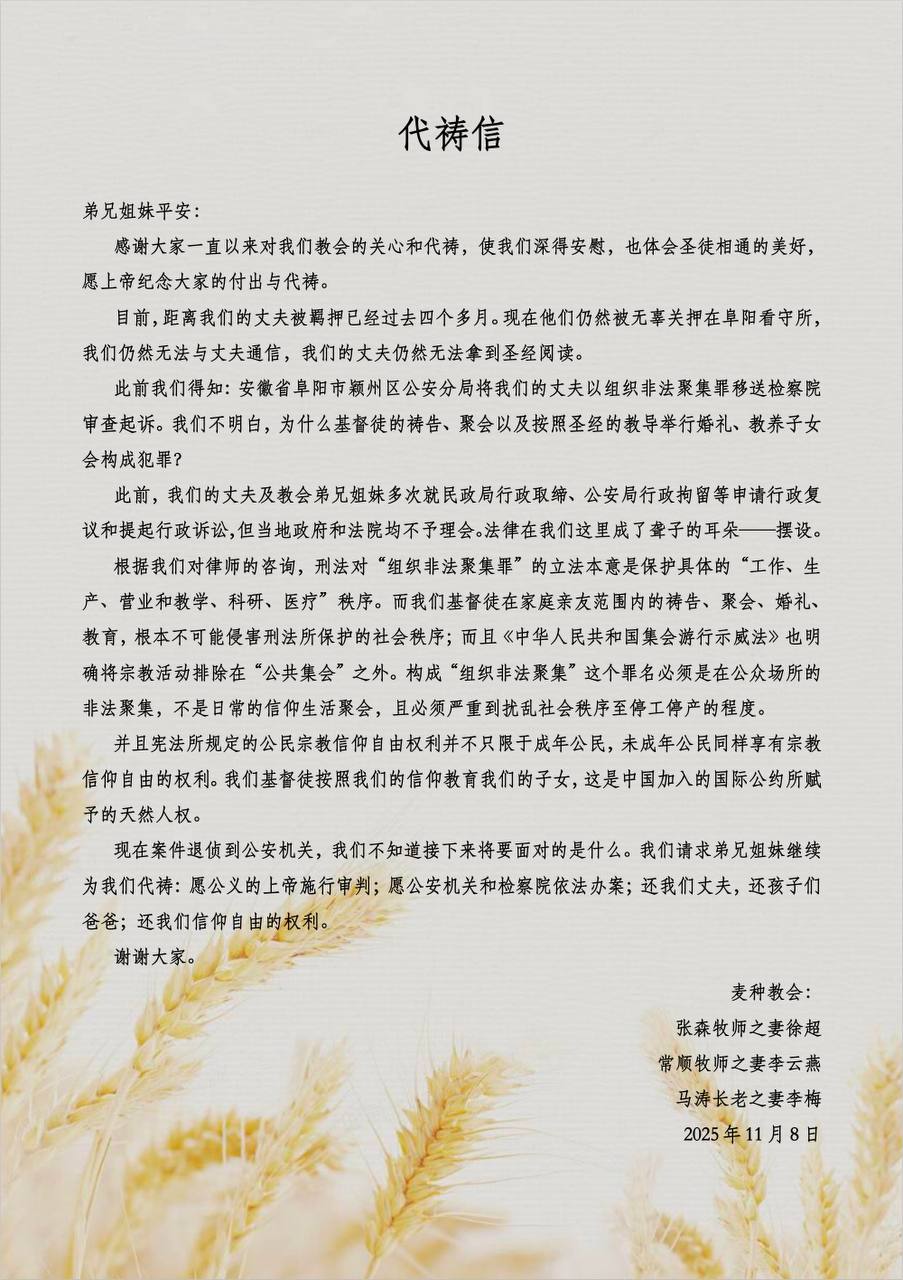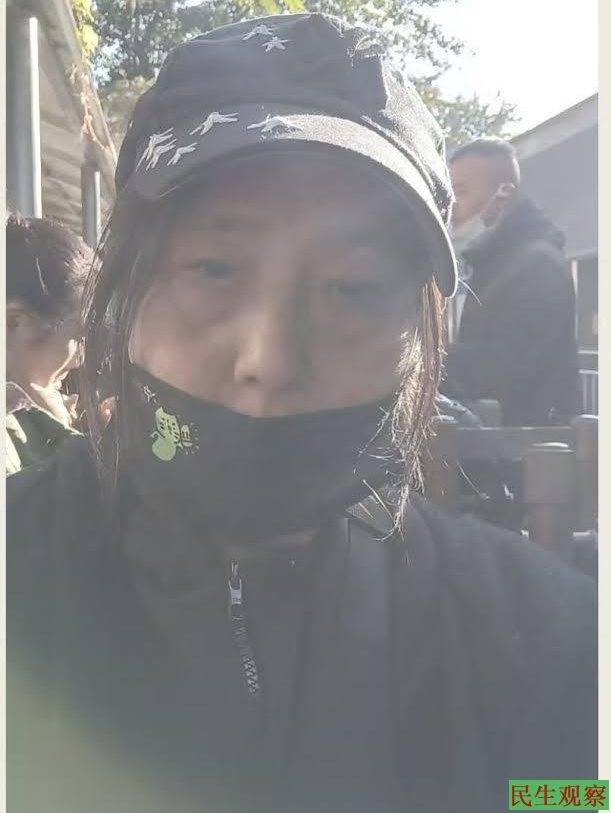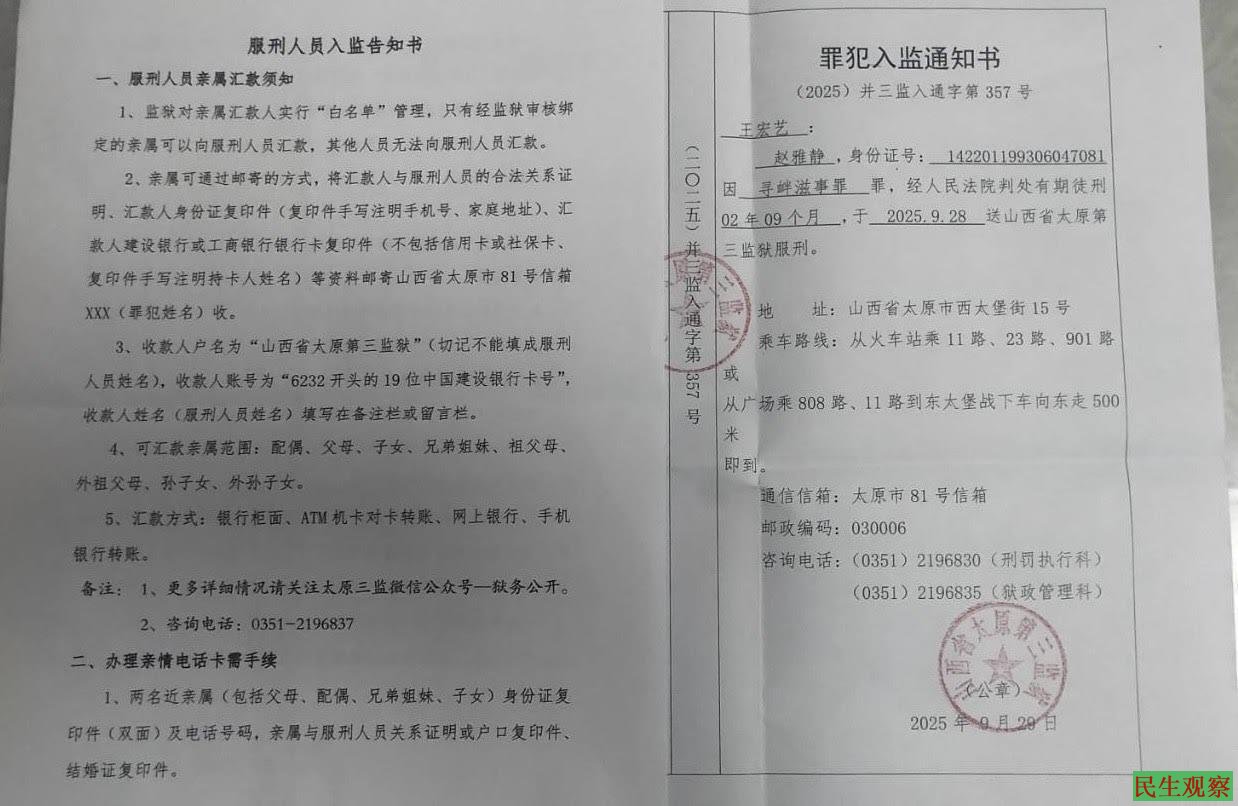编者按:宗教信仰自由本是公民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也是人的基本人权,然而在中国,自中共1949年执政以来,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天主教就遭到中共政府的全面镇压与迫害。中共为控制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强迫其加入官方管控的“三自教会”,并把所有不为中共控制的非官方宗教团体都定性为邪教,把《圣经》定为邪教书籍,许多家庭教会被强行取缔,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遭到中共的抓捕监禁、酷刑折磨、判刑劳改,至少上万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以下是现流亡法国的中国基督徒王冬冬向本协会的投稿,讲诉了他因信神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的真实故事——
我叫王冬冬,我家一共4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1997年,因母亲信主后病得医治,从此我们全家都信了主耶稣。信主后,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依靠,家里不管临到大事小事,我们都祷告主、按照主的教导实行,我们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一家人其乐融融。但中国是无神论政党掌权的国家,一直以来都逼迫宗教信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家人在村里遭到了所有人的歧视和排挤,村干部也常来我家恐吓我们,让我们放弃信仰。
年幼时的心灵伤害
2001年,我们全家都接受了主耶稣再来的福音——全能神的末世作工。就在我们为迎接到主的再来而欢喜快乐时,2002年春的一天,我父母在家里给人传福音时被人举报,月山镇派出所的约8个警察开着两辆面包车到了我家,他们以“非法传教”为罪名抓走了我爸爸和三个弟兄姊妹,还抄了我的家,搜走了所有信神书籍,爸爸被非法扣押一天后放了回来。从那以后,警察隔三差五就上我家搜查,威胁恐吓我们,并要把我爸抓去劳教,爸爸为躲避抓捕被迫逃离家乡,躲起来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失去了幸福的家,母亲被迫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649x365.jpg)
在学校里,同学都因我家信神而弃绝、讥笑、毁谤我,只有哥哥和我一起玩,我内心孤独无助;中共警察的第一次抄家,对我心灵造成的伤害,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到了今天,我看到警察都特别地害怕,一紧张就会心慌,全身会控制不住地发抖。
2003年,我12岁,一次传福音时被警察抓捕了,逃脱后我被迫辍学。我只上了4年学,所以我至今只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后来全国爆发了SARS,所有外地人必须回到当地,警察也不敢到处乱跑抓人了,我爸才回到家。虽然村干部还是常常上门警告不许我们信神,但我们仍然小心谨慎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家庭大变故
2011年11月,中共在河南省展开了“雷霆行动”。他们在各地疯狂抓捕、迫害基督徒,我们当地陆续有29个带领被抓,很多人的家被抄。因被抓的人里面有直接负责我父母本分的上层带领,为了安全,父母不得不离开家躲避抓捕。一开始我以为中共的“雷霆行动”过去了,父母也就回来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不久后的一天,我还在外尽本分,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家的院子里停了几辆轿车,我有种很不详的预感。因我实在担心家里,就在傍晚冒险回了家。那天一进村子,我就感到气氛很不正常,以往热闹的村庄今天格外安静,当时我压抑地喘不过气来。一进家门,我就愣住了,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门窗全开着,灶上的火还在烧着,一盒子的鸡蛋被吃光了,鸡蛋壳扔了一地,家里就像被土匪洗劫了一样。 当时我来不及想更多,赶紧骑着摩托车通知那些认识我家的弟兄姊妹,害怕通知晚了,弟兄姊妹也会受牵连。
第二天,我赶紧到弟兄姊妹家打听情况,原来是上层带领被抓后经不住警察的酷刑,把我家保管教会钱财的事告诉了警察,警察来我家是为了抢夺教会的钱财,幸好我父母离家时已经把教会钱财转移走了。后来我了解到,那天我回家时,警察刚抓走了我的哥哥,并在我家等了一阵,试图把我和父母一家4口全部抓走。
母亲离世
警察为了掳夺教会钱财,继续搜捕我父母。后来,我躲到一个弟兄开的钢铁厂里,与弟兄姊妹隔绝了。为了掩护自己,我留了长发,并染成了黄色,把自己装扮成社会青年。我的心时刻为父母、哥哥担心,为那些被抓捕的弟兄姊妹担心。在煎熬中过了5个月,一天,我无意中在接待我的弟兄家看到了一封信,开头写着: “王冬冬的妈妈去世了,请不要告诉他……”当时我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从小到大没离开过的妈妈已经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心如刀绞,瘫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真想冲出去再看妈妈一眼,但却不能,甚至我连大声呼喊“妈妈”的自由也没有,因为中共的眼线还在紧盯着我们,我这样做只能给爸爸和弟兄姊妹带来麻烦、危险。那天晚上我整晚没睡,我一遍遍地想起妈妈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妈妈对我和哥哥的爱护……可是现在我永远见不到妈妈了,是中共把我们迫害得骨肉分离、家破人亡!
短暂的重逢
因中共的追捕越来越升级,我不能在当地待了,就和几个弟兄姊妹准备到四川继续传福音,临走前我意外地见到了爸爸。那一刻,我惊呆了:怎么这么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苍老憔悴,眼睛肿得很大,脸看上去都变形了,我和爸爸抱头痛哭。爸爸告诉我,他和妈妈为了躲避追捕,几经辗转躲到了一个山洞里,因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成天担惊受怕,妈妈病倒了又不敢去就医。一天晚上8点左右,妈妈带着对孩子的牵挂离开了人世,爸爸说那晚他很想放声大哭,但却不敢。妈妈的离世成了我和爸爸心里永远的痛。原本我以为此后至少能和爸爸在一起,没曾想,我们到四川的第一天就被警察盘查,又被迫分开逃亡。
无辜遭受牢狱之苦
2013年初,警察在云南,贵州,四川实施大抓捕。3月28日,我们福音队的负责人被抓。29日早上9点多,我约了两个姊妹在广元的湿地公园见面,不到五分钟,突然二、三十个荷枪实弹的特警包围了我们,并拿枪指着我们。一个老姊妹想跑,几个警察冲上去一脚将她踹翻在地。两个警察二话不说扭住我的胳膊使劲往后一拉一提,我的胳膊像断了似的疼。他们将我们3人戴上手铐,分别押上警车带到了派出所。
警察先后把我带到广元市南河片区三个不同的派出所拍照备案,后来他们抢走了我的两部手机、手表和1500元人民币,一辆价值2000多元的电动车也被没收。搜完身,他们喝令我双手抱头,光脚蹲在冰冷的地上不准动,我稍微一动就被猛踹在地,蹲了2个小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审讯室拷在老虎凳上整整6个小时,不让我吃喝拉撒。期间,所长进来一看到我就指着我说:“就是他!”通过警察的对话得知,还有90多个警察在外面蹲点,准备把弟兄姊妹一网打尽。
傍晚,苍溪县国保大队的警察将我押至苍溪县看守所,警察扒光我的衣服搜身,剪掉我衣服上的所有拉链和扣子,将我和杀人犯、强奸犯关在一起,十几个人挤在狭小恶臭的监室里,吃喝拉撒全在屋里。
第二天上午9点,警察把我拷在铁椅子上提审了3个小时,问我的个人信息和教会情况,我不能让弟兄姊妹落到他们手里,跟我一样受迫害,就说我是孤儿,什么也不知道。警察恶狠狠地威胁我:“你小子不老实交代,老子整死你!”我还是不说,他们就将燃烧的烟头弹到我脸上。之后的半个多月,我天天被提审恐吓,他们拿出很多弟兄姊妹的照片让我指认,其中有个受过酷刑的弟兄的照片,就是我们福音队的负责人,照片上的他脸部肿胀,胡子很长。之后,他们又说出我和弟兄姊妹打电话的内容。我这才知道他们已利用摄像头、电话监听、录音等对我进行了至少近半年的跟踪。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所有犯人每天都要刷锡纸长达10个小时,这个锡是有毒的,人长时间呼吸到肺里就会得癌症,工作时间长了每个犯人身上都长了很多红疙瘩,痒的难以忍受,嘴里也全部溃烂了。犯人集体感冒了,管教不给我们药物,还说:“死不了,不用看病吃药!”还逼着我们继续干活。我听一个犯人说:“光我们一个监室,每年就能给他们创收100多万。”在监室里,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陈米,白水煮烂菜叶,没有盐没有油,每餐都吃不饱。除此之外,每个监室里都安装了2个摄像头,24小时监视,犯人没有一点隐私。
我被关在看守所三个月零十一天,每天度日如年。

“回家”
被释放后,当初我身上带的钱警察一分都没有还给我,我身无分文,只能沿街乞讨去找弟兄姊妹。为了躲避中共的监视我深夜进了一个接待家,接待家的阿姨看见我凄惨的样子,哭着说:“孩子,你可回来了,你这几个月到哪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也被害死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母,感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三天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继续传福音。
走投无路 逃亡法国
2014年,我在拍摄组尽本分。5月28日,中共炮制了“山东招远杀人案”栽赃抹黑我们教会,随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大规模调动武警与正规部队抓捕基督徒。6月份,负责我们拍摄组联络工作的姊妹被警察抓捕,紧接着周边六个小区带领也相继被抓,我们被迫多次搬家。后来,拍摄组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我们被迫解散,分散躲藏。
2014年下半年,中共政府扬言把所有因信神被抓过的人再抓回去判刑坐监,很多弟兄姊妹又被抓捕了。我实在走投无路,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于2015年5月6日逃到了法国。临走前也没有见到我爸爸、哥哥,现在我虽然逃到了民主自由的法国,有了暂时的自由,但一想到年近花甲的父亲和哥哥还在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日子,我就很为他们担心,也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事实上,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因坚持信仰而遭受着中共的残酷迫害,活在红色恐怖之下。但因中共的严密封锁,这些事实鲜为人知……
责任编辑: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