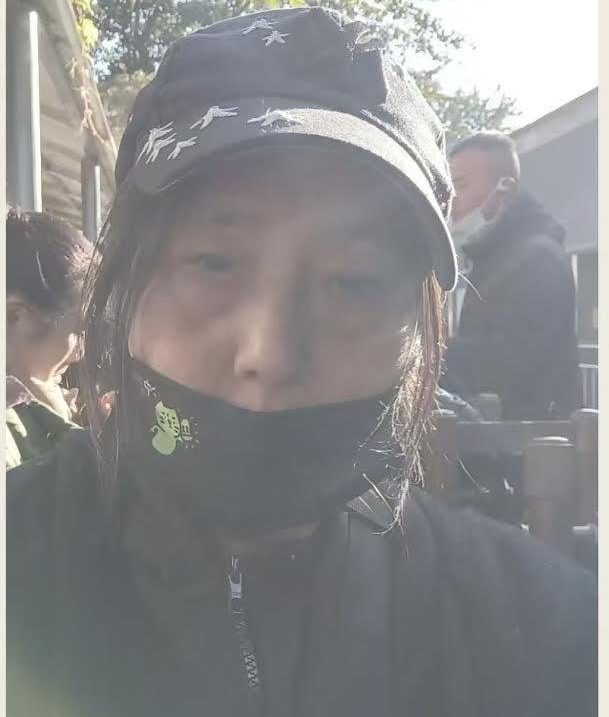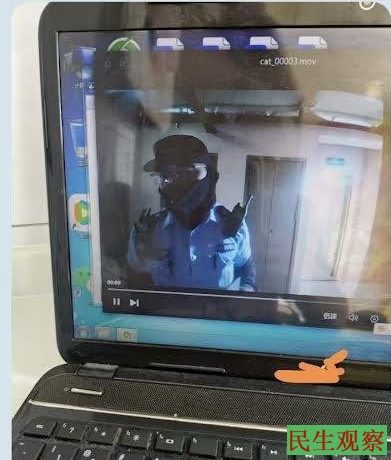阿卜杜哈克木·伊德瑞斯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也是著名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罗珊·阿巴斯(Rushan Abbas)的丈夫。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如今身在何处。
作者:阿卜杜哈克木·伊德瑞斯(Abdulhakim Idris)

亲爱的妈妈:
2017年4月25日,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您的声音。
现在过了1095天,离我们上次通电话已有3年。我还记得,当时您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不要再给您打电话。
2001年我们在德国见面时,您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儿子,眼睛能看见的我们都见到了,往后的几年我们要挺过去。除了敬畏安拉,我们谁都不怕。你要走好自己选择的道路。”妈妈,我了解您,我了解您的勇气。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您怕成这样?到底是什么能迫使一位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要给她打电话?
自从2010年来到美国,我天天给您打电话。我在1982年就离开了家,当时太年轻,很多事情都理解不了。我去和田一所地下宗教学校上学,这意味着我再也无法帮您干家务活,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没能尽上家庭义务。
1986年我出国留学,您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我。亲爱的妈妈,您不知道,1989年前往阿拉法特参加朝圣活动时,我们和其他在国外的维吾尔留学生就毕业后下一步计划进行了讨论。当时我们想寻找关于我们也许能为自己的家园做些什么的答案,怎么做才最有利,最后,大家决定移民西方民主国家。1990年9月9日,我没有征得您的同意就跟朋友到了德国,并在那里定居。我“为了理想背井离乡”,迈出了实际的第一步。虽然我的人离您很远,但我的心靠您很近,妈妈。
一想起那天您让我不要再给您打电话,我现在仍然感觉很难过。一年多以来,为了保护兄弟姐妹,我和他们彼此切断了联系。现在,我和您也无法再联系。我仍然记得,您挂断电话后,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低着头,泪水夺眶而出。我被莫名的伤感笼罩着,悲伤和永远的骨肉分离占据了我的心灵。
我早已知道,由于(中共)持续的压迫,我的兄弟阿卜杜热依木(Abdurehim)被一家令人厌恶的汉族人折磨(“结对认亲”)。一些人在政府的“结对认亲”运动下强行入住您的家中,公然冒充是您的家人。我曾经问过您,“那些厚颜无耻的客人是不是还在?”您却只是深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自从我们的家园1949年被共产党霸占后,中国政府就一直想摧毁我们家族的声望和自豪感。他们没收了我爷爷的马和财产,接着还拆掉我们漂亮的大庭院,毁掉我们的花园天堂。您当时也没有这次这样的反应。现在,恶毒、羞辱和耻辱攻入了我们的安乐窝,我们的家园,甚至我们的最后一个堡垒。妈妈,难道这就把您击垮了吗?我那勤劳坚忍的爸爸变得那样无助,您是为此痛苦吗?我的姐姐妹妹遭到虐待,我那没有私心的兄弟阿卜杜热依木遭到奴隶般的折磨,是这些让您绝望了吗?是不是因为您无辜的孙辈命运堪忧把您吓到一个地步,以致您切断与我的联系?
我知道您十分清楚该如何忍受艰辛、克服大难。妈妈,到底是什么暴行迫使我天使般的妈妈喊不出声来?东突厥斯坦,文明的摇篮,已经落入了黑暗中。
自从我与您失去联系的那一天起,我就心乱如麻,震惊不已,整个人都被击垮了,我很快变得沉默寡言,常常魂不守舍。有时候我垂头丧气,满腹心事,有时候我会失去理智,我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过了一百多天,亲戚给我发来一条消息,说我兄弟阿卜杜热依木被判21年有期徒刑,我的姐姐妹妹全被关进了集中营,还告诉我我的父母命运如何不好说。在信息的最后,我得知您家的大门被上了锁,房子已被查封。当我问起您的孙子孙女的情况时,被告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快要死了,这条消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内心被无助、脆弱的感觉压垮了。消息开始不断传来,说我许多朋友的亲人也被抓进了集中营。
记得有一次您对我说:“儿子,如果将来有一天边境封关,我们失去联系,你可以放心,我们很好。你好好照顾你的妻儿,不必担心我们。”妈妈,当时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说,但现在我终于悟出您那句话的意思了。您真有先见之明,居然能预知我们的家园日后发生的事。
这段时间,我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您,您在我的每一个心思里,在我的内心深处。无论我走到哪里,不管我在做什么,心里想的全是您的往事、您的音容笑貌。我的生活被忧虑和绝望填满。想到无法打听您的下落,不知道您和爸爸会遭遇怎样的恐怖经历,会不会感觉很无助……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极度痛苦。
邪恶的中共政府剥夺了您和几百万无辜的维吾尔兄弟姐妹的人格、尊严,强迫你们在监狱和集中营中渡过一生。我们已尽最大的能力告诉全世界。我们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合作,前不久还成立了“声援维吾尔人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Uyghurs),这些平台的宗旨都是为了终止邪恶。
2018年9月5日,在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差不多500天后,您儿媳妇参加美国一个著名智库的座谈会。她说到我们家有人失踪的情况,同时还指出了集中营的恐怖状况,东突厥斯坦已变成了活脱脱一个奥威尔式的警察社会,她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6天后,中国政府绑架了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乌鲁木齐的一名退休医生,他们还在阿图什市绑架了她60岁的阿姨,以报复罗珊的维权活动。
在这段艰难的时间,我忠诚而勇敢的妻子罗珊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她不仅是我的知己,而且在人权事业的道路上,她已成了我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我们夫妻二人继续在拯救我们同胞的道路上探索,同时努力为那些无法发声的群体发声,捍卫毫无防卫能力的无辜维吾尔人民。然而,在我和您失去联系的那一刻,几百万人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而这个自由世界的国际社会却保持沉默,媒体也不报道,似乎这一切都被隐瞒了起来。
您儿媳妇整天整夜坐在电脑前忙着给记者们发消息。她一直在努力让这些史无前例的暴行引起人们的关注,捍卫您和几百万(维吾尔)人民的权益。“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行动”的妇女们倡议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举办全球性抗议活动,持续了22个小时。
我告诉身边一些非维吾尔族的人,说中国(政府)不许我和父母家人有任何的联系,也不能打听他们的情况,人们很难相信我说的话——在21世纪这个信息时代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妈妈,如果您见过我妻子,您就知道她在许多方面很像您,你们都是一样的爱憎分明。她从不偏坦任何人,从不害怕任何事,也从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您知道她是怎样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对抗中国政府,那该多好。她不断接受记者采访,一直在问:“我姐姐在哪里?我公公婆婆在哪里?我的亲人在哪里?我几百万同胞在哪里?”我可以想像,您一定会替她感到无比的自豪,您一定会爱她、敬她、赞她,因为您一定会劝勉她加倍努力,鼓励她要更坚强。
妈妈,我好想听到您的声音,好想听到您说的话。我想跟您谈谈心,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想跟您说我现在很知足。我想告诉您,在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US President Trump)发言时,您儿媳妇因努力捍卫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受到表彰,当时在场的还有副总统彭斯(Vice President Pence)、众议院议长佩洛西(Speaker Pelosi)、国务卿蓬佩奥(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还有其他高官、政界人士、外国外交官、新闻界人士和经济学家。我想看到您满意而骄傲的神情,在我谈到您儿媳妇取得的成就时,您一定会轻轻地点一下头,露出慈祥的笑容。
我和罗珊夫妻二人这辈子将为您和维吾尔人民捍卫人权。我们时刻都在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我们醒着。在我们所到之处——论坛上,伊斯兰组织中,清真寺里,大学内,我们将继续为您、为所有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人民发声。我们必须联系听众和平台,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土耳其到加拿大,从欧洲到美国各州,我们必须继续唤起人们的关注。
我们必须捍卫人权,只有这样,我们家园争取祷告权利的呼声才不会被喊停,我们尊贵的民族才能永远不消失,监狱才能被关闭,集中营的高墙才能被推倒,压迫的锁链才能被砍断,整个东突厥斯坦才能重获自由。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他们在和平与繁荣中生活的权利,我们正竭尽所能,为东突厥斯坦再次独立作出贡献!
这就是我们年轻时移民西方国家时的远大志向其中的一项内容,对于现在世界各地维吾尔人社群的建立和存在,以及为了维吾尔人的事业而专门成立的组织,我心存感激。
今年年初,我们去了加拿大,期间认识了生活在温哥华的章闻韶(Shawn Zhang)。他是第一个通过卫星图像识别并证明东突厥斯坦确实存在集中营的人,也是研究集中营的国际知名专家。他向我展示了一张卫星图,上面是新疆博斯坦(Bostan)居民区,旁边就是贝格·图格曼(Beg Tugman)的坟墓,挨着我们家的房子——那是我离开34年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房子。我仿佛穿越了眼前的屏幕,我感觉我的灵魂已出窍,不再受我的控制。我打开一扇扇门跑进屋里想看到您,妈妈!我在里面寻觅您身影时,我的心脏跳得好快,但是,我找不到您。
我问章闻韶,“哪一处集中营离我父母家最近?”他马上引着我们穿过我们家附近的水库,指向在新阿瓦提沙漠(New Awat Desert)兴建的一个大型集中营,具体位置位于罕艾日克镇北部,新艾日克西部(West of New Erik),拉斯奎镇西北部。他告诉我们,集中营正在那一带扩建。然后,他向我们展示这一处集中营2019年12月29日扩建的部分。我想可能我多数兄弟姐妹都被关在这一处集中营里。我尽量不去想像我的姐姐和妹妹在集中营里遭受怎样恐怖的身心伤害。但是,我真的想像不出您和爸爸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我迫不及待地打听我们家附近的几处孤儿院。章闻韶给我们看了(卫星图),我再也忍不住去想,我的侄女、外甥在里面被洗脑,放弃民族身分、母语和宗教信仰,我感觉浑身都在颤抖。
章闻韶还向我们展示了我妻子她们家在乌鲁木齐诺盖清真寺对面那栋房子的3D图。但是我们温柔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医生已不住在这栋房子里。妈妈,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妻子十分伤心。从我们面前的大银幕上,我们看到无数的集中营和监狱遍布我们的家园。我们还看到,达阪城区集中营比(当地)整个镇还大,而乌鲁木齐的监狱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之一。
妈妈,我好担心。来自武汉的新冠病毒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影响?您还面临哪些难处和痛苦?吃的喝的够不够?我妻子的兄弟姐妹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加入到劳役大军被强迫送去中国内地工厂工作?我那几个年幼的侄女、外甥被当成孤儿送去了哪里?我的兄弟姐妹中有没有谁因强摘器官丢掉了性命?我兄弟阿卜杜热依木是不是真的被转移到了中国内地某座监狱?妈妈,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谁还活着,谁永远地走了,但我希望你们都平安无恙。我为您、为所有维吾尔人和普天下的人向安拉祷告,但愿这个斋月能带来祝福、宽恕、怜悯和拯救。
我相信,每天黎明前晨祷时,安拉会垂听几百万母亲的哭声。我相信我们的人民必然得救。黑暗过去,光明一定会来临。真理必定会占上风,我们将战胜这股邪恶势力。
亲爱的妈妈,我们总会再见面的,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来世!
阿卜杜哈克木·伊德瑞斯
华盛顿
2020年4月25日
来源:寒冬